作为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颌面外科的主任医师,下班后仍去医院查看病人情况,早已成为俞光岩的日常。俞光岩住在北大口腔医院的宿舍,几分钟就能走到医院。每当自己有重要的手术病人,他都会在夜间步行前去探望。

走到病人床前,俞光岩俯身查看问询。这位病人在口腔医院做的手术,俞光岩却关注他眼部创口的情况。这是手术成功与否的关键。

一周岁的时候,史东旭不停地发烧,烧了二十八天。他告诉妈妈,自己感到眼干,难受。等到退烧慢慢恢复后,他发现了自己没有了眼泪。
“我的儿子,他就没有眼泪啊。”妈妈说。那之后,史东旭患上了严重的干眼症,视力不断下降。
12岁时,患了眼科疾病的史东旭,来找口腔科医生求助。他来到北大口腔医院,进行左眼的下颌下腺移植替代泪腺手术。俞光岩作为主刀医生,将史东旭左侧唾液腺中的下颌下腺,移植到左眼处,代替他的泪腺。手术后,史东旭的眼干症状大大缓解,能够顺利生活了。
目前,对于重症干眼症患者来说,下颌下腺移植手术是最重要的治疗方法。而手术的复杂程度,却远超他们的想象。
史东旭慢慢长大,但是重症干眼症,导致他的右眼视力依然不断下滑,从12岁的0.4下降到了0.1。重症眼干,也会令人非常痛苦。怕风怕光睁不开眼睛,还伴有灼痛。长大后,史东旭学了民族器乐演奏。但由于视力原因,对他而言,背谱子比看谱子更加容易。

今年,33岁的史东旭,又一次来到北大口腔医院,找到了俞光岩。这一次,他希望能够通过俞大夫的帮助,提升个人的视力。
俞光岩翻看史东旭的病例资料。电脑里存档的照片,21年前还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可爱的模样逗笑了医生和护士。

俞光岩结合之前的病例,研判了史东旭的情况,决定用唾液腺移植代替泪腺手术,为他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对于重症眼干,俞光岩做过显微解剖的研究,发现移植的腺体的血管导管系统像树枝一样分布,而把这一部分去掉后,仍然能使留下的部分保持完整。术中如果直接切掉一部分,可以预防移植后腺体过量分泌。
从12岁,到33岁,这台手术,史东旭跨越了21年。这21年间,俞光岩带领团队,不断钻研术式细节,现在的水平与当年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手术当天,史东旭的母亲也从山东赶来北京,在手术室门口等待儿子。

手术开始了,这是一场需要多科室紧密配合的接力战。在麻醉科医生对史东旭进行了全身麻醉之后,俞光岩主刀精准地取出了史东旭的右侧下颌下腺,为史东旭的右眼找到了新的“泉眼”。
下一步则是将这口“泉眼”安置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为之后的“南水北调”做好铺垫。这一个位置就是人脸的颞部,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医学上叫做“移植”。这一步听起来容易,真实的操作起来可并不简单。在人体这个精密的构造里,一个器官的“螺丝”并不能完全适配另一个器官的“螺母”,它还需要医生在“施工”时进行精密地“改装”。

取出移植腺体,吻合相应血管,切除多余成分,手术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另一位北大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医生蔡志刚的精准操作下,史东旭的下颌下腺被“改装”成适于移植的大小,并顺利移植至颞部。紧接着,北京同仁医院眼角膜科的主任医师吕岚接过这场手术的“接力棒”,将颌下腺导管接入史东旭的眼部。
手术台边,一圈医生们高度专注着操作。持续了四个小时后,其中一位医生抬起头,对俞光岩说:“俞老师,我们一切妥当,可以吻合血管了。”

手术顺利完成。俞光岩盯完所有细节,才踏出手术室。晚上,他又从家里走到医院的复苏室,来到病人床边。
“史东旭,睡着了没有啊,来看看你。”操着一口温声细语的浙江普通话,俞光岩告诉史东旭,他的手术顺利,现状良好。“头几天,有些辛苦,再坚持坚持。”俞光岩微笑着伸手,轻轻扶了扶史东旭的床头。

21年前,史东旭做了左眼手术后,引流管对眼膜有一定压迫,12岁年幼的他没有及时向医生反馈不适感,导致视力提升并不理想。这一次,医护团队和史东旭都着重关注,在精细的术后护理下,21年前的遗憾,没有再次发生。
一次手术就完成移植,套管不再摩擦角膜影响视力,辣椒素刺激腺体分泌,史东旭的左眼右眼见证了一种创新术式20年的发展。他坐在病床上,眼泪不断落下来,笑容挂在嘴角。

总是笑眯眯的俞光岩,刚成为一名口腔科医生时,觉得“32颗牙齿,没什么可做的”。
老家在浙江诸暨农村,初中毕业后,俞光岩就打算回家“去当农民了”。回去后,恰逢当时赶上筹建农村合作医疗,“当时人家觉得我中学毕业,在农村里多多少少算有点文化的,觉得我人也不错,就让我去当赤脚医生。”
不久后,绍兴地区卫校要招生,俞光岩就开始了正式、规范的学医。培训期快结束时,绍兴地区医院招新职工,俞光岩被招了进去,正好分配到了口腔科,由此开始了他与口腔医学的缘分。
当时的口腔科工作比较单纯,就拔牙、补牙。俞光岩觉得,“每个人嘴里就32颗牙,整天不是拔就是补,好像有点太简单了。”但慢慢做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口腔科也不那么简单,同样是为病人处理问题,这其中大有学问。
在绍兴地区人民医院口腔科工作了5年后,俞光岩在1976年成为了浙江医大口腔系第一届学生;1979年,考上了北京医学院口腔系(北京医学院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的研究生,硕士毕业后,留校在北京医学院口腔医院工作,就一直到了今天。2009年,他从北大口腔医院院长位置上退休,2016年到中华口腔医学会来当会长,从始至终都没脱离过口腔专业,该看门诊看门诊,该上手术上手术。
现在,担任中华口腔医学会名誉会长的他,作为一名口腔科大夫,治了眼科的病。面对重症眼干这项世界性的难题,他以“下颌下腺移植治疗重症干眼症”,施救了许多病人。
眼干是一个眼科中很常见的疾病,普通的眼干没有过大问题,滴滴眼药水基本上就可以了,但是对于重症眼干,保守治疗的效果并不好,所以重症眼干对眼科来说还是一个疑难性疾病,在整个世界范围也都是一个难题。

1997年,俞光岩的学生,也就是现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副院长蔡志刚教授,从德国带回信息:那里的专家把唾液腺移植治疗重度干眼症的目光从腮腺转向了下颌下腺。唾液腺外科正是俞光岩的研究专长,他便成立课题组,决定将这一项目开展起来。
俞光岩通过把下颌下腺带着血管和导管转移到颞部,跟颞部的血管吻合上,把导管转移到眼眶,用下颌下腺分泌的唾液替代泪液。这个手术很复杂,技术方面的要求很高,但是效果不错。1999年这一技术被正式应用于临床,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这还远远不足,术后还存在重症泪溢的病人。为避免重复手术给大概率出现重症泪溢的病人带来负担,俞光岩又研究出预防方式,使泪溢的二次减量切除手术率由80%下降到了30%。
俞光岩遇到过一个病人,一个9岁的小女孩,因为药物过敏导致重症眼干、视力低下,生活不能自理:饭就放在床头柜上,但她看不到筷子,要妈妈来帮她找,走路也需要妈妈扶着。
俞光岩带着课题组给她做了下颌下腺移植手术,一只眼睛手术后,女孩的视力就恢复到能自己走路了。后来又把另一只眼睛也做了手术,她能自己骑自行车上学了。
口腔颌面外科的专业范围,在外国相对较窄,可以做拔牙、创伤、颞下颌关节之类的手术,但不能做肿瘤、唇腭裂手术。中国的人口多,病人也多,练就了外科医生的手术技巧,口腔颌面外科的专业范围要比国外更宽泛,包括牙槽突外科、正颌外科、口腔颌面创伤、口腔颅颌面肿瘤、唇腭裂等畸形矫治、颞下颌关节疾病等等。
本来可能会遭受终生痛苦的孩子,因为下颌下腺移植新技术,改变了自己和全家的命运。“这就是研发、应用和推广新技术的意义所在。”俞光岩说。
北大口腔医院以此技术治疗了200多例重症眼干病人,是全世界范围内治疗病人数最多的。

夫人吴立玲也从事医学工作,俞光岩与夫人所在的基础医学院病理生理教研室展开深度合作,从临床与基础相结合的层面进一步研究了唾液腺的分泌机制,在一系列临床与基础相结合的研究工作后,形成了重度干眼症不同时期、不同情景的治疗常规。
老两口在这栋70年代后期建起来的小楼,一住就是几十年。2000年左右,楼体做抗震加固,院里在农业大学旁边建了两栋新房,居住条件都更好。但是考虑到这栋老楼距离北大口腔医院近,更方便自己时不时去看看病人、去办公室,俞光岩和夫人又搬回了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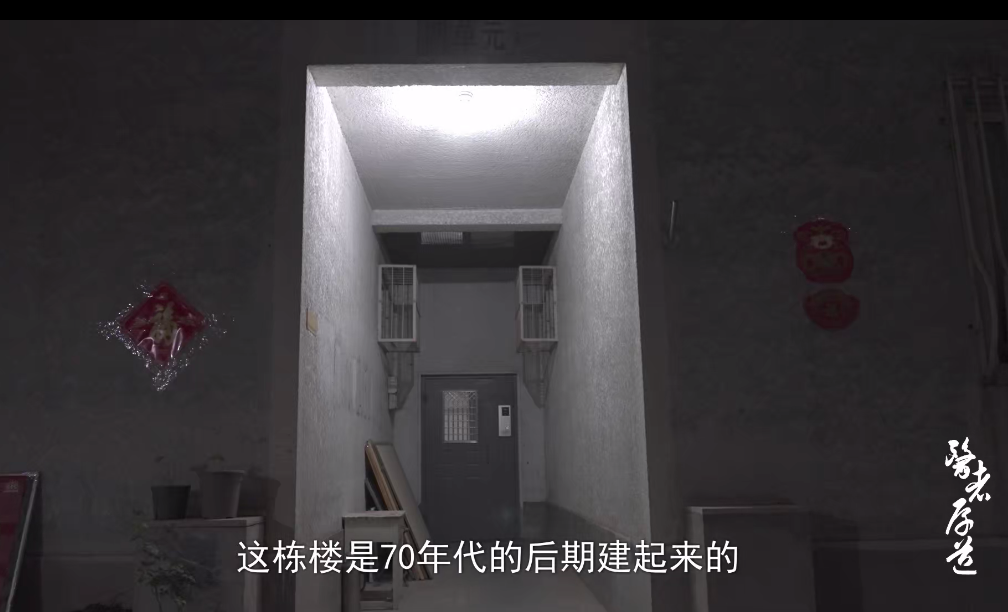
俞光岩的情感、笑容、关注,几乎都投注在了找到他的病人身上。曾有学生开玩笑说:“病人不听话,得治一治。”俞光岩摆摆手正色道:“要想提高病人的依从性,不能靠‘治’,而是要靠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
几十年前,俞光岩值班时,一位年轻医师告诉他,一位患有早期口底癌的病人不太配合第二天的手术安排。
原来,这位病人当时上医院看病是因为口腔黏膜溃疡,但没人告诉他得的是口腔癌。晚上值班护士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偷偷去看了病历。看到病历上写的是“癌”,霎时间心灰意冷。他担心癌症无法根除,治疗开销还会拖累新婚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已经做了自我了断的打算。
俞光岩在术前找到这位病人,耐心与他谈话,将早期癌预后相对乐观、治疗经验比较丰富的情况向他一一说明,像一位朋友一样:“好多病人治疗效果挺好,照样生活、照样工作。”
从此,他一直心怀感恩,常常利用自己的职业技能,来为忙碌于病房内外的医护修理冰箱、录音机等电器,与医生护士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许多年后,病人又一次与俞光岩谈起当年的事,依然忘不了当年那番术前谈话。“俞大夫,手术前那晚的谈话,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我都印象深刻。那一番话,救了我一条命。”
现在,这位病人成为了电影公司的技术骨干,由他担任制片人的电影已经上映,他向俞光岩报喜。“病人朋友取得了成就,比我自己获个科技奖还要高兴。”俞光岩话音未落便笑逐颜开。
医生、病人和家属,这三种角色,俞光岩都体会过。“如果没有全面、精湛的医疗技术,不能解决患者的问题,那厚道行医就成为一句空话了。”这种“救人一命”的自豪感,激励了俞光岩的儿子,他也和父亲一样,选择了学医。